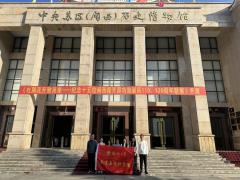他是个颇自负的人。
毕竟在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像柳庄这样的偏远小镇里,如他这般上过高中,还拉得一手好二胡的人并不多见。
说起柳庄,那就像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小镇一样,带着文革风暴肆虐过的残余尾声,过着春种秋收,除草犁田的平稳日子。对柳庄人来说,不管外面世界怎么闹腾,政策怎么翻覆,土地分来分去也就是那几亩,牛分来分去也就是那么几头。这世上变动的东西太多了,要是整天价就跟着在后面瞎转悠,那等到蹬腿闭眼的时候啥也捞不着。所以,心坎上就装着自个儿和几块薄田,踏实。
他就住在平静的柳庄最东边的一隅,离柳庄中心十分远,周围几乎没有人家,只有丛丛的荒草和白绒绒的芦苇。他的住处小且简陋,干裂的泥巴墙上糊着稀疏的石灰,就像是五十多岁的老妇女皱巴巴的脸上的廉价白粉,轻轻一碰就扑簌簌往下掉。房顶是几捆蓬松干枯的茅草,下面垫着几块薄木板,勉强算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屋子。这所丑陋的屋子就巍巍地站在波光粼粼的东坎河边,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驼背老人拄着拐杖临江而立,还时不时抖心挖肺地咳嗽几声。
柳庄人对他的身世并不熟悉,对他仅有的了解,也就是他在县城里上过几年学,然后就到了柳庄当教书先生。他的出现并不引人注目,还是他定居下来的三四天后,人们听见东坎河上游隐约飘来的二胡声,才惊异地发现柳庄来了个新住户。至于他为何放弃上学来到柳庄,为何总是孤身一人,他的父母亲戚都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有人试图询问他,但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让他们欲言又止。突然出现的他,沉默寡言的他,念过书识过字的他,神秘的他,与只知道种地过活的柳庄人之间好像有一层隔膜,将他们分成两个世界。这种陌生又带有轻视意味的隔膜让柳庄人渐生反感,很快,他就被孤立了,像是他那座东坎河边的孤独的房子。他就一个人守着遥远的星球,漂浮在虚无寒冷的宇宙间,只是在给村里孩子们上课时与村人见上两面,平时就在自己的屋子里拉二胡给自己听。无疑,二胡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灵魂的伴侣,在他被梦魇般的往日记忆的纠缠,绝望又寂寞的时候,是潺潺的二胡声,填满了空虚的心房。他无法倾诉,但是二胡的每次运弓都滴着血和泪。
他自我感觉像是一只婷婷白鹤孑立于一群苍灰的雀鸟间。
孤独的白鹤踽踽独行在河畔七年,伴着声声二胡临风梳羽,引吭独歌,突然撞见了一朵开的落落寡合的莲花。第一次看到她,他的心便仿佛在三月的春风里游走了一回,弱水三千于他便没有了任何意义。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名叫蓁蓁,在柳庄人眼里,她的皮肤白皙的像白雪雪的发面馒头,头发乌黑像是抹了蓖麻油,水灵灵的眼睛就好似粉嫩嫩的滴露白桃。上天就把这样一个浑身闪着光的姑娘哐的砸在柳庄,像一道亮烈雪白的闪电,劈咔一声,让柳庄人感觉眼前唰地一亮。
许多年后,在一个寒意如刃,秋气逼人的大雨夜,虽然与光明告别许久,他的一生却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眼前明亮而又快速地幻化。万花筒似纷碎的幻相中,一个印象脱颖而出,越来越深刻,直到五颜六色的碎片停止飞速转动,时间静止。他想起了那场下乡运动。那场让蓁蓁离开上海温柔乡,下凡到柳庄,下凡到他这个穷怪的书生面前。从前,他觉得那场运动是月老的红线,拴住了两个人的姻缘。直到现在,他才哗地明白,那场运动也是一截命运的绳子,他陷得越深,被绳子牵的也越紧,落的深渊也越深。而看似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其实也就是两个孤独至饥饿的人惺惺相惜的偶遇。
在他见过蓁蓁后的那段日子里,柳庄去东坎河下游洗衣服洗菜的人,会影绰听见东坎河那边的二胡声昼夜不停,几乎从未中断过。从激越的《江河水》,到黯哑的《春江花月夜》,乃至《空山鸟语》,乃至《姑苏行》,流畅的胡琴声伴着哗哗流动的河水以及有节奏的锤洗衣物的声音终日萦耳而不绝,那些好事喜谈的大娘们总会在忙碌的间隙交头接耳一番,“可准是看上人家蓁蓁姑娘了”,“只在咱们这穷地儿,他也算个出挑的,但那姑娘生的跟雪团儿似的,肯定瞧不起他呢”“是哟,毕竟是金丝雀儿,还是要回笼的”。
不知是那白净孤僻的青年总是红着脸从身旁经过,还是初春的风多少吹了些闲言碎语进了蓁蓁的耳里,她渐渐地喜欢在河边洗衣服时凝神细听从上游飘来的二胡声,听着听着就入了神,暗地想着他的二胡怎么可以拉的这样好。那声音极具穿透力,仿佛可以看见细细的琴弦在怎样的颤抖,绷紧了的蛇皮琴面是怎样的震动,而那琴弓,琴弓一定是一小捆纯白色的马尾毛,不然怎么这琴声总是那样纯净,那样哀愁。这一切都不同于她在城里常听的钢琴,那样的轻巧华丽,每个音符都飘在半空中,飘在耳朵旁,但怎么也进不到心里。她开始想见到他,说说话,谈谈胡琴,或者发生点什么,发生点什么她在上海那座纸醉金迷的禁锢之城无法体验到的故事,发生点什么在她原来偷看过的书上的情节,她觉得那会是人生中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
或许接下来的事就是顺理成章了,譬如村里动员大会上的偶遇,譬如吞吞吐吐伴随着抓耳挠腮的暗示,譬如飞红羞赧的脸颊和绞来绞去的衣角……后来,柳庄的人们在插秧或除虫,捡麦穗时,经常会看见,一个衣襟飘扬的瘦高男青年骑个自行车,带着一个漂亮白皙的姑娘在田垄上疾驰而过,有时姑娘的手里会拿着一束醡浆草,有时两个人的头上都带着点地梅编成的花环,带着明艳的色彩在灰扑扑的柳庄大街小巷里风驰呼啸而过。他的二胡曲再也不会自拉自听,他会在东坎河边找块突起的土丘上坐着,神采飞扬地拉着《紫竹调》、《千里草原》或者是《江南春色》,带着蓁蓁或摇橹于水乡之间,或策马奔腾在万里草原之上。蓁蓁总是坐在他身边,托腮细听,看着他上下翻飞的手指是那么的修长灵活,来回运弓的姿势是那么的潇洒。她突然觉得,人生怎么可以这样美好。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在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结,谈吐优雅举止不凡的公子们外,还有这样一个青年,他透彻的像块水晶,他让她感到新奇。
这段时间,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无论他们携手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周围人群既妒又羡的眼光。“哟,能耐不小,能找到这么洋气的对象,你可是高攀人家了!”经常有人这么对他说,语气让人听不出来他想表达什么。每每这个时候,他都只是淡然一笑,不作理会,然而他的心里却也是明镜儿般的清楚,若不是那场运动,蓁蓁怎么会离开那金子做的城市,又怎么会看上他这个除了二胡就一无所有的农村青年,于是,他的心里竟有那么一些地感谢那场运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两人的感情也如火如荼,他们固执的认为,除了像《上邪》里那样的事发生,他们才会分开。
那年的春天不知为何特别寒冷,多雷雨。天气多变地像是反复无常的国家政策。
那一天,他在屋里思考怎样把《桃夭》谱曲,明天就拉给蓁蓁听,表明自己的心愿。为着这个,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桃花儿一样鲜活活红艳艳粉嫩嫩的蓁蓁,作为自己的新娘该是多么美。自己虽然没有了家人,但也对父母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一种告慰。自己父母在自己年少的时候就早亡,留给他一把胡琴,将自己托付给县城的二叔父,在县城第二附中上了几年学。后来文革爆发,自己学上不成了,二叔父又被革职,拉上街游斗,二叔父一家无法增添他的开支,委婉的将他赶出门。无路可走的他怀抱着胡琴,背着稀薄得可怜的行李流浪到柳庄,在东坎河边默默地搭起了属于自己的简陋的小屋,不会种田的他找了个教书的差事,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将蓁蓁娶过来之后,他就准备再去县城闯一闯,凭自己二胡的功底,又知文懂字,偌大一个县城,总有自己谋生的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他心中鼓荡着久违的豪情壮志。他似乎看见自己与蓁蓁的未来是那样光明。即使不光明又怎样?去他的!蓁蓁就是自己的太阳。只要蓁蓁在自己的身边,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
突然,外头轰隆一声响雷如凌厉的利刃猛地劈开了他激昂的思绪。他默默站起,走到窗前,看着滚滚乌云缓缓压进,感受着巨雷给大地带来的细微震颤,他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但他又甜蜜的回想一下,觉得这段时间是那样美好,美好到应该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它变坏。
应该吧。
1980年5月8日,国家新的政策如那声响雷般轰隆一声横空出世——允许知青返回城市。一辆黑的发亮的小汽车在夜里就那样毫无征兆地带走了蓁蓁。她像是一株被临时栽在这片地上的花朵,在那边找到更好的花盆后又那样栽了回去,不知去向,与这片土地再无任何瓜葛。
他在看完村头贴的国家最新政策后,像是心脏猝不及防地被砍去了一块,鲜血横流。料峭的寒风吹过心脏留下巨大的空洞,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绝望与无助。前天还一起在柳庄西南角那棵大柳树下手执诗经,一起读着“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昨天还在为她练习新曲准备今天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为何到了今天,兴冲冲起个大早带着二胡而来的他只看见空无一人的屋子,突兀地竖在平地上。他无法想象,蓁蓁在被带走时是怎样的心情,有没有对他产生不舍,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也无法想象蓁蓁有没有与家人产生对抗;他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蓁蓁会不会从那个他今生都高不可攀的城市偷跑回来,再次与他相聚。在意识到蓁蓁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后,他颤抖着嘴唇,像是中了魔一般的念叨着:“走了…..走了……是啊,那才是她的家,她的父母怎么会同意我们在一起,说不定人家早就有了婚约,都是我傻,我傻啊……你走吧……就当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说到恨处,他把二胡往地上哐地一掼,劣质的木柄瞬间断成两截,尖锐的白色木楂刺眼地露在外面。他蹲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地哭着,最后直接像喝醉了酒似的趴在地上,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晌午,他慢慢爬起,在村人们幸灾乐祸的眼光中一瘸一拐地踱回自己的小屋。
躺在床上,他只是以泪洗面,眼流不停地往下流,粗麻布缝制塞干草的枕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竟生了霉。细菌不断地感染他的眼睛,开始时,眨一两下就没事了,后来他觉得觉得眼睛越来越疼,像是有谁在他的眼里撒了一把钉子,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眼疼的煎熬,勉强下床,请了一个蹩脚的村医,开了一剂虎狼药,第二天,在长时间的头晕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原本的教书先生也干不下去了,生计已经成了一个关乎生死的难题。他凭着触觉艰难地把断成两截的二胡用胶带层层缠绕好,因为看不见,手臂被尖锐的断口刮得鲜血淋漓。他准备在街头卖艺。可是,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又有几个人有那个闲心驻足欣赏他的琴声呢?更有甚者,最爱看清高的他沦落至此的凄惨,佯装好心为他带路,却把他生生往沟里带,看着他连人带琴摔进肮脏的污水里的那种快感,已经被不少无事的村民视为好玩的报复。他也只是慢腾腾地从沟里站起,摸索着污水里的胡琴,然后起身一言不发,一瘸一拐地向不知是哪里的地方走去。
人们再见到他时,他己经是胡子拉碴,衣衫不整,双眼只剩下眼白,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在别人的葬礼上拉着哀切的乐曲,靠别人施舍一些残羹冷炙过活。每每拉到动情之处,他自己也是声泪俱下,浑身颤抖,浑浊的双眼中不停地掉着泪珠……
有一天,不知是哪家调皮的孩童,在玩火时不小心点燃了他家的茅屋。东坎河边熊熊燃起的的大火让柳庄人目瞪口呆,但是考虑到没有自家的土地在那,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救火。谁知道他有没有死在那场大火中呢?反正自那后柳庄里就再也没有响起过苍凉的二胡声。不过也有人说,起火的那天,他正好不在屋子里,在某个葬礼上拉琴。更有人说自己在相距二十公里的清水村赶集时,看见了一个很像他的人在街头拉琴,面前摆个破烂的碗。
两三天后,人们很快对关于他的话题失去了兴趣。夏天到了,柳庄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劳作。村人们说,今年雨水特别的足,来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